【1】这种事情怎么说呢,你说不说的其实也没啥用,对吧……所以就这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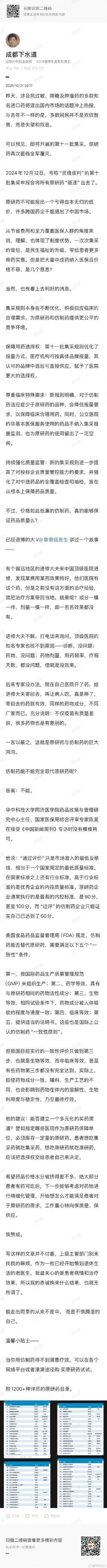
【2】原研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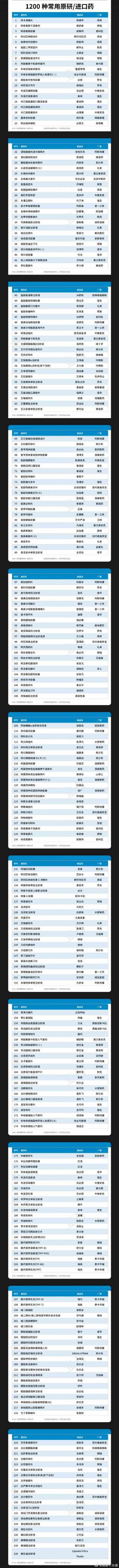
【3】@劳东燕2004
这是一位朋友针对锡林浩特集中采集男性DNA事件所做的评论。
DNA数据库与权力的隐秘延伸
星辉
9月,一则几乎被忽略的新闻从内蒙古锡林浩特传出——警方自9月5日起,集中采集辖区男性居民血样,录入地方DNA数据库。官方解释称,这是为了“完善公民身份信息”、“防范走失”与“便于证件办理”。然而这份看似温和的公告,却打开了一个沉重的问题:当国家开始系统性地采集男性DNA,我们究竟站在怎样的社会门槛上?
人脸识别、指纹录入之后,DNA信息的收集,是信息化治理的又一次跃进。但它与前者不同——指纹识别的是“我”,DNA识别的却是“我们”,是一整个家族、血统乃至潜在亲缘网络。它不仅是个体识别技术,更是一张铺开的家系地图,是人类身体最深处的社会档案。
一、从“破案利器”到“家系网络”:权力的技术延伸
在刑事侦查领域,Y染色体家系排查技术确实带来了革命性突破。白银案、南医大案等长期悬案的告破,都离不开Y-STR比对。其原理是:男性的Y染色体从父系稳定遗传,因此只需家族中一人入库,便可在家族范围内追溯潜在嫌疑人。公安系统称这种思路为“以Y找群,以常锁人”。
然而,这种“找群”的逻辑也意味着:任何一个男性个体的DNA信息,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整条父系血脉。换句话说,一个人被采样,整个家族都被纳入了隐形的监控半径。技术的精准,并没有消解它的社会风险,反而拓展了国家治理触角的生物学边界。
这正是Y库的本质所在:它并非只是侦查工具,而是一种家族化、血缘化的社会治理手段。它让“嫌疑”的定义在生物层面上被扩张,从具体的个体,延伸到潜在的基因共同体。
二、没有立法的“技术合法性”:当程序失语
更令人警惕的,是这项措施的法律基础。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DNA样本的采集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与案件直接相关人员。锡林浩特警方却以“完善公民身份信息”为由,对辖区所有男性采血,这显然越过了法律授权的边界。
在法治原则中,“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公共权力的底线。任何数据收集若未经明确立法授权,就属于越权行为。而此次行动,却以“非强制”、“自愿”之名掩盖了行政压力的实质性存在。在一个小城镇,警察上门、村医随行、村干部动员,所谓“自愿”到底还能剩下多少空间?
技术合法性与程序正当性之间的断裂,恰是当代中国信息治理最突出的风险所在。我们太容易接受“技术中立”的神话——只要它有效、便捷、能破案,就被默认为“合理”。但在法律缺席、监督缺位的前提下,技术的中立只是幻觉,它所嵌入的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公权在采集,个体在被采集;信息在积累,隐私在消失。
三、“姓氏基因”与“社会谱系”:隐私的再政治化
Y库技术的核心,是对男性家系的追踪。它依赖的基因片段被称作“姓氏基因”,因为Y染色体的传递方式与传统父系社会的“传姓”极为相似。这种巧合极具象征意义:它把中国社会那种深植于血缘与宗族的文化逻辑,数字化、技术化地复活了。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生物血缘化”的治理模式,恰恰与现代公民身份理念背道而驰。现代国家建立在法律关系上,而不是血缘关系上;公民应当是基于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个体,而非某个家系的成员。当国家在生物层面上重新标定公民身份——哪怕只是出于侦查需要——它无形中就把“家族”重新拉回了政治场域。
这种“隐私的再政治化”,远不止技术问题。它意味着:公权力不再仅仅管理公民的行为,而开始管理公民的身体与血统。信息主体的“可识别性”变得无限延展:你的身份不仅由身份证号定义,还由你无法改变的遗传密码定义。
四、侦查效率与公民权利:技术扩张的悖论
支持Y库的人常以“侦查效率”为理由。确实,DNA比对让积案侦破率提高,成本降低。然而,效率并非社会治理的唯一目标。任何治理手段,都应当在效率与权利之间保持平衡。
极端地说,如果效率至上,那么安装家家户户摄像头、强制佩戴定位芯片、收集所有人的基因信息,都会让犯罪几乎无所遁形——但那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社会吗?现代法治的核心,不是最大化控制,而是限制控制。真正的文明,不在于破案速度,而在于不因破案而牺牲无辜者的权利。
DNA数据库尤其特殊,因为它几乎无法“退出”。一旦信息入库,就可能永久存在。Y染色体的“家系代表性”使得数据即使当事人去世,也能被无限追踪。这种时间上的“永生”,让数据治理的责任也变得永久——而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应的法律、技术与伦理机制来承担这种永久性。
五、从技术治理到身体政治:未来的隐忧
Y库的出现,是技术治理逻辑的一次极端化表达:治理者掌握的信息越多,社会就越“安全”。然而,安全的另一面是控制。当个体的身体信息被系统化、编码化、数据库化之后,身体就不再是私人的,而成为一种可被调用的资源。
在国际上,DNA数据库的伦理争议早已持续多年。欧洲国家普遍采用“比例原则”,即只有在严重案件、确有必要时方可采集DNA,并设定严格的销毁期限和用途限制。即便如此,仍有大量质疑指向“基因歧视”“数据滥用”“家族关联追踪”等问题。而在中国,尚未有任何法律明确规定DNA数据库的采集程序、使用范围、监管机制与退出制度。我们正处于技术发展远远超前于法制保障的阶段。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生物信息治理的逻辑,一旦确立,将极易扩展。今天是男性Y染色体,明天可能是SNP检测、外貌预测,乃至疾病基因筛查。技术从来不会自我约束,它总是在被发现“有用”之后,迅速滑向“泛用”。
当DNA数据被纳入公民身份系统,不再只是侦查工具,而是社会治理基础设施时,公民的身体将不再完全属于自己。这种从“社会管理”到“身体管理”的转变,是当代技术政治最深刻的趋势之一。
六、沉默的社会与缺席的立法
更令人忧虑的,是公众的沉默。锡林浩特事件曝光后,舆论反响平淡。没有大规模质疑,也没有官方解释的充分回应。相比人脸识别、个人征信等议题,DNA似乎距离普通人太远,技术太复杂,难以形成情感共鸣。这种“知识盲区”恰恰成为最危险的空间——因为不了解,人们更容易默认“无害”;因为不抵抗,权力就能更顺滑地推进。
然而,隐私的丧失往往不是一次剧烈的剥夺,而是缓慢的滑坡。从指纹到人脸,再到DNA,每一次技术扩张都以“便利”“安全”“防走失”之名出现,每一次公众都在“反正我没做坏事”的心理下逐步退让。最终,我们也许会生活在一个完全透明却彻底不自由的世界里。
七、立法滞后的代价:当监管永远在“追赶”
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立法。自1990年代DNA数据库兴起以来,中国尚无任何专门法律对其采集、存储、使用进行规范。国家标准《法庭科学DNA数据库建设规范》仅关注技术质量,而非权利保护。结果是,DNA采集在制度层面处于灰色地带:既非明确合法,也非明确违法,只要挂上“破案”“防走失”的标签,便可堂而皇之地执行。
这种“灰色治理”是风险最大的状态。没有法律约束的权力使用,意味着责任无法追溯,滥用无法惩戒。信息一旦泄露,不仅会揭开家族隐私、非婚生子、领养关系等社会禁忌,还可能在就业、保险等领域引发基因歧视。技术人员、行政部门、第三方承包公司、数据管理者……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潜在的风险源。
当DNA数据库的建设与扩张持续推进,社会必须追问:谁来监管采集行为?谁能访问数据库?信息保存多久?当事人是否有权要求删除?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再先进的技术都可能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
八、当“血缘”成为治理逻辑
Y库并非单一的技术项目,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权力、隐私与安全关系的真实态度。它所代表的,不只是侦查工具的进步,更是一种治理思维的转向——从社会控制到身体控制,从行为监督到基因识别。
它让我们重新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在追求安全与秩序的名义下,我们愿意把多少身体的、私密的部分交出去?而谁又能保证,这些数据不会被用在另一个“合法”却危险的方向?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比犯罪更难防范的,是技术被权力驯化后的野心。那时,真正被锁定的,不再是犯罪嫌疑人,而是我们每一个被数据库标记的普通人。
【4】鲜为人知的是,豆包(Doubao)还有一个海外版本:Cici。它与豆包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布,应用图标同样是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女性卡通头像,只不过 Cici 的头像头发比豆包的更长。该应用有区域限制,在中国和美国都无法使用,这也解释了它为何比豆包更加鲜为人知。
但字节跳动(ByteDance)一直在悄悄地向英国、墨西哥以及几个东南亚国家的用户推广 Cici。Meta 广告库显示,Cici 在 10 月份仅在墨西哥就投放了 400 多条不同的广告,大多数广告都强调该模型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以及完全免费使用的事实。目前,Cici 也正在英国和菲律宾进行广告宣传。在 TikTok 上,这些国家的创作者已经用#ciciai 等标签分享了数十条关于 Cici 的赞助视频。
得益于这次市场推广,Cici 应用的下载量最近出现了明显增长。根据市场情报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墨西哥和英国等市场,过去三个月里,这款应用一直位列 Google Play 商店免费下载应用的前 20 名。例如,在墨西哥,Cici 在过去一周内每天都是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量最高的免费应用。在英国,周四时,Cici 是苹果 App Store 上第九受欢迎的免费应用。
- WIRED

【5】分析:社交媒体的兴起与西方民主的衰落(节选)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皮尔德斯长期研究这些问题,他这样阐述这种复杂性与模糊性:
“从技术革命的整体利弊来看,印刷术曾助燃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并不仅仅是钉在教堂门口,正是新发明的印刷术使它迅速而广泛地在德国和欧洲传播。”
“约瑟夫·戈培尔称收音机是‘第八种强大力量’,他说,如果没有收音机和飞机,纳粹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今天我们并不希望失去自由媒体、收音机或飞机。”
尽管如此,皮尔德斯认为,“推特和有线电视(也是传播革命的一部分),加上初选机制取代政党大会的做法,共同在特朗普最初的选举成功中起了重要作用。”
皮尔德斯接着表示:
“毫无疑问,新技术对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正在经历的政治碎片化起到了显着推动作用。这些技术让政治参与更广泛,但也使得对政府施政的挑战更易被动员,并且可能持续不断。技术革命在很多方面削弱了政府有效治理的能力,而一旦政府无法做到有效治理,民众的愤怒、失望、不信任甚至更糟的情绪将会持续加剧。”
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技术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
在10月2日发表于Persuasion网站的一篇文章《是互联网,笨蛋: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根源?要怪就怪屏幕》中,福山在花了近十年时间研究全球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后写道:
“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从更广泛意义上说,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推动了全球民粹主义的兴起,并决定了它所呈现的独特形式。”
福山进一步指出,互联网的出现,既能解释民粹主义崛起的时间点,也能解释它为何带有如此浓厚的阴谋论特征。
在当今政治中,美国红蓝两派不仅在价值观和政策上分歧严重,甚至在事实认知上也南辕北辙,比如谁赢得了2020年总统选举、疫苗是否安全等基本问题。
两派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空间中,都相信自己在为美国民主的生死存亡而斗争,因为他们在威胁民主秩序的本质认知上就存在根本分歧。
福山表示:“如果没有互联网,特朗普关于2020年选举的叙事根本不会引发任何关注。”
【6】@懒得生虫
刚看了一个霉帝(dems)农民介绍为啥霉帝农民在川&ICE搞了这么多针对非移民的raid后,还是支持川的视频,挺有意思。意识形态外,单就ICE这方面也又非常自私的理由,主要就是因为非遗由于没身份,去留相对自由,工作不想做就会走,并不算稳定的劳工。所以越来越多的雇主开始倾向于走合法的H2A签证的临时农民工签,但这种签证的问题是,一方面有很多行政上的程序,农民觉得搞那么多书面申请很麻烦。第二,需要给H2A提供吃住,并且开符合当地标准的最低工资,所以这类人成本比较高。第三,通常对这类工人的需求时间不长,就6-12周的农忙,不忙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养”这些工人,他们觉得不划算。
于是,解决这些需求的中介也就应运而生了。我的理解是这类中介跟hk的菲佣印尼帮佣的制度差不多,H2A是由中介出面办理,然后就靠中介把人派到有需求的农场,农场只需要提供最低限度的吃住即可。由于中介往往会在把人弄到美国以后把护照收走,工人实际上被送去农场后就被困住了(霉帝农场通常离城市也很远),这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合法slavery。
而这些工人除了按最低工资工作外,往往会被逼迫去农场正当工时外的其他工作(不给加班工资),住条件极其差的大通铺,甚至也有工人被x侵犯。他们想要逃也很难,一是因为护照没有了,二是农场主都有枪,另外也是因为农场会用他们在南美的家人来威胁他们。由于他们是合法申请,家庭住处背景都被农场&中介拿捏,随时可以找当地gang去威胁。
这时候就要说回为啥农场主都支持川了。2021年,FBI冲掉了南乔治亚州一个大型human trafficking的catel(图1)。其中被走私的工人都是合法H2A身份的,但他们依旧被